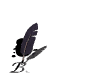五、叩稟「修不離靜,藉靜堪寂滅」之有關常識供參
本堂副主席孚佑帝君 開示:
林生問:『靜』乃影響修行成敗之關鍵,修唯心繫此『靜』
永不離,亦唯知所藉靜者,堪期煉就『此心於寂靜』乎?
帝君答:然也,凡夫之心,常向外馳,心一旦馳散,則鎮
日渾渾綽綽,妄想紛飛,提不起道心,故修行首要即是要讓
自心寂靜調順,方能深入法味也。
林生問:不識透『本心』,就頗難以『靜心』乎?
帝君答:然也。甚多修行人喜在事相上打轉,而心波難止,
自然無法靜心,故六祖壇經言:「不識本心,學法無益。」
即是此理。
林生問:只一個『靜』字,即使在芸芸修子中亦少有人能臻
『靜心』、契『靜境』,何因?
帝君答:因人生活於塵世中,就必須與色塵緣境打交道,在
聲色當中討生活,故許多人雖奢言修行,但多自制力不足,
仍為色塵緣境所迷惑,而放不下聲色享受,放不下功名利祿
,放不下貪愛情感,有者不但放不下,還想樣樣企求擁有
,因此終難『靜心』、難契『靜境』。
林生問:以臻昇何心境?堪稱『真靜』。
帝君答:心不妄動。
林生問:不論有修無修,為什麼我們就是始終無法做到
『靜心』之地步?
帝君答:無修之人,其心鎮日向外馳求,故無有『靜心』
之時。而有修之人又多始勤終懈,無有恆心,或雖參禪打
坐有了瑞相,便起我慢,心中漣漪不止,故亦難達到『靜
心』之境地也。
林生問:其實我們這一顆心總易患『我執』而不覺,可謂所
思所想,卻幾乎無時無刻無不念念著在己身心上乎?
帝君答:此即是現今修子之弊端,現今之人書籍經典讀得多
,功夫用的少,平日修行總喜在文句上論功夫,或是鸚鵡學
舌般談法,卻沒有落實在日常生活中改變習氣,因此除了患
一般凡夫之執著外,更多了『貢高我慢、法執或分別心』,
而蒙蔽了明心見道之覺性。
林生問:吾人只要心著『酒、色、財、氣;恩、愛、名、利』
任一塵染而勘不破,也就甚難以靜下『此心』乎?
帝君答:當然。生死塵勞自貪欲起,而『酒、色、財、氣;
恩、愛、名、利』無非是為了色身,無非是為了欲求,有欲
有求則談何靜心之來?
林生問:或『有私、有欲,有求、有執』者,就難靜心乎?
帝君答:是的,此乃無庸置疑也。
林生問:或只要『有一念之生、一絲之妄動』者,就難靜
心乎?
帝君答:靜心之境界,不在制念不起,而是在心不隨念頭
起舞,不因念頭而生起自我問答對話,此可於禪坐中訓練得之。
林生問:或凡患『我識』較重者、那就更難控制『此心』乎?
帝君答:當然。根、塵成識,即代表作用已起,識心必如
猿猴一般,一刻也不得安靜也。
林生問:如何習『禪坐』,以沉澱『此心』、靜定『此心』
乎?
帝君答:禪坐者,調身、調息、調心也,身調好即可調息
,然一般人於禪坐調息時,必然妄想紛飛,念頭迭起,故當
念起時,應以無迎拒心、無好惡心、無是非心、無得失心,
亦即「不思善、不思惡」之方式觀察念頭,則不論是善念
、惡念、不善不惡念,皆會當下遁形無蹤,而得心之靜定,
即調心也。
林生問:如何藉靜定,以『生發智慧』乎?
帝君答:定者『息慮靜緣,內不動心,外不著相』也。
當一個人能息慮靜緣,內不動心,外不著相時,就不會到
處攀緣,降伏嗔恚,故攝心為戒,因戒可生定,因定即能
開發智慧、去惑證理,破諸煩惱。
林生問:如何藉發慧,以去除諸『煩惱』與『執著』?
帝君答:有真智慧者,常觀『色』是苦、是空、是無常、
是非我(無我),觀『受、想、行、識』亦是如此,從
它們的『生起、存在、消失』,皆如實觀察、如實了知,
自然心中不會升起煩惱、執著也。
林生問:修得禪徹『此心』堪入覺,藉明覺以觀照身心與清
淨心靈而得解脫乎?
帝君答:然也。以覺悟靈明之心來觀照世間、觀照自心,
必可得到解脫也。林生問:成道證佛非難,但看孰能『靜
定此心』,全在『此心』用功夫乎?
帝君答:然也。修行是如人飲水,冷暖自知,只要一點一
點的去做,就如登山一般,當爬到了應有之高度時,廣闊
的平原就會盡收眼底,霎時你會豁然開朗,看到真理,
認識真理也。